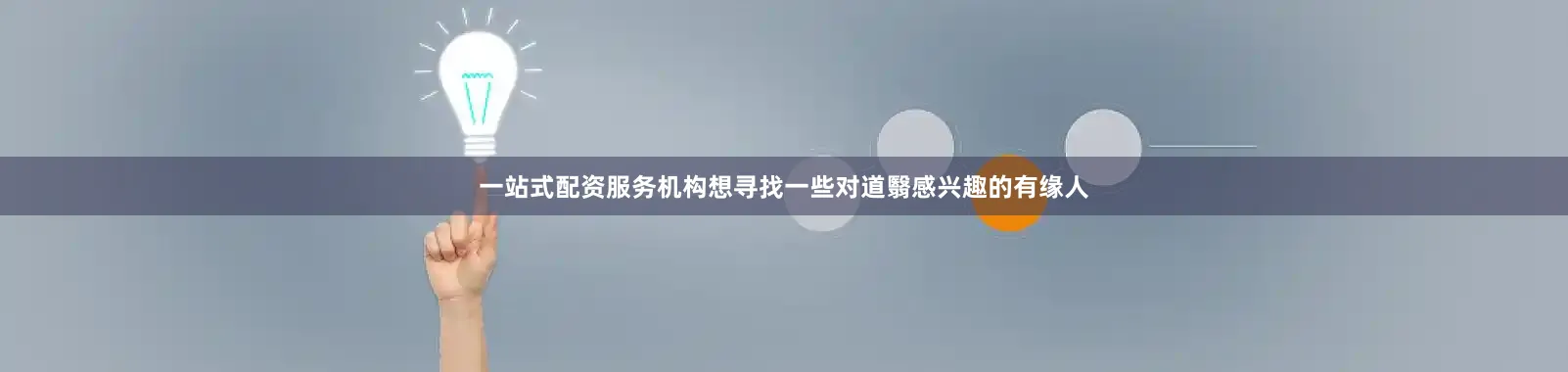1935年,中国的西南大地上正上演着一场关乎生死的千里跋涉。红军的队伍沿着蜿蜒的山路翻山越岭,他们得在大渡河前杀出一条活路,否则,这支历经千难万险才保存下来的革命火种,可能就要被湍急的河水彻底浇灭。
这条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大河,到了四川西部突然变得脾气暴躁。它像一匹挣脱了缰绳的野马,在两岸刀削斧劈般的悬崖峭壁间横冲直撞,浪头拍在石头上,溅起的水雾能遮住半边天。可就在这时候,红军的前锋部队已经站在了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渡口。这里,就是他们必须突破的天险。
时间得倒回几个月前。1934年10月,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"围剿"打得异常艰难。当时,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,采取"堡垒推进"战术,在苏区周围修筑了数千座碉堡。红军战士每天都要面对飞机轰炸、炮火覆盖,粮食弹药越来越紧缺。最困难的时候,战士们每人每天只能分到半斤糙米,子弹要数着打,受伤的同志连绷带都用树皮代替。

在瑞金的临时中央会议上,毛泽东同志抽着旱烟沉默了很久。他提出的运动战建议早被否决,现在根据地只剩六个县城,红军主力被挤压在狭长地带。那天夜里,周恩来同志提着马灯走进指挥所,摊开地图说:"必须走了,趁还有突围的余地。"朱德总指挥默默点了点头:"留得青山在..."
10月16日傍晚,中央红军八万六千余人秘密集结在于都河边。老乡们连夜架起浮桥,妇女们把最后的口粮塞进战士们的干粮袋。没有人说这是永别,但每个人都知道,这一走,不知何时才能回来。星光下,队伍像一条沉默的火龙,向着西南方向的未知险境蜿蜒而去。他们不知道,这场被迫的远征,将创造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。
1935年5月,当红军的先头部队终于望见大渡河的滚滚河水时,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河对岸的山崖上,隐约能看到敌人的碉堡,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河面。
红军先头部队的指挥员算了一笔账:这几艘船一次最多载二三十人,来回一趟得个把小时。要把几万红军全部运过去,至少得十天半个月。可后面的追兵离这儿只有几天路程,等船运完人,黄花菜都凉了!
就在这时,有人提到了泸定桥。"泸定桥?"战士们议论纷纷,"听说那是座铁索桥,横在河面上,走起来晃得厉害。"整座桥全靠13根碗口粗的铁链撑着,每根铁链都有几吨重,固定在两岸的石墩上。桥面上铺着木板,走上去"吱呀"作响,可比起摆渡过河,这已经是条捷径了。
但这时候蒋介石给刘文辉下了死命令:"炸掉泸定桥!绝不能让红军过河!"可刘文辉却并没有听蒋介石的,他把桥面上的木板拆了,只留了铁链子。
后来总会有人问,当初是什么原因让刘文辉没把桥彻底炸了呢?难道他也是我党人士?
想了解这件事,我们就得从刘文辉的故事说起。

刘文辉1895年出生于四川大邑县的富户家庭,家里有十几亩薄田,父亲是个教书先生。这个看似普通的农家子弟,却在16岁那年揣着全家凑的盘缠,考进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。1916年毕业时,他穿着笔挺的军装回到四川,开启了长达三十年的军阀生涯。
1920年代的四川各方军阀为抢地盘打得昏天黑地:成都平原上,刘湘的部队在成都城头架着大炮;川南的刘文辉带着人马在宜宾收烟税;川西的邓锡侯在绵阳囤积粮草。
1923年刘文辉和侄子刘湘两人联手击败杨森时,刘湘的部队负责正面进攻,刘文辉带兵绕后截胡。可等打下重庆城,刘湘却连夜把盐税仓库的钥匙换了人。叔侄俩从此结下梁子,1933年的"二刘大战"更是打得惊天动地。刘湘从成都调来德国造的山炮,刘文辉在雅安用竹筏搭浮桥运兵,这场混战持续了整整一年,最后刘文辉带着残部退到西康,成了人人喊打的"西康王"。
退守西康看似落魄,实则暗藏玄机。这个连接川藏的咽喉之地,虽然只有雅安、康定几座破城,却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。刘文辉让人在泸定桥头设卡收税,大烟土、麝香、虫草从藏区运出来,茶叶、丝绸往西藏运,光是过路费每年就能收几十万银元。他还在康定开了个"边茶贸易公司",把四川的砖茶换成藏民的羊毛,转手卖给英国商人,硬是把个穷山沟经营成了"小天府"。
1935年5月,蒋介石的追剿令像催命符般飞到康定。这个满脑子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委员长,既想借红军消灭异己,又怕地方军阀趁机坐大。他给刘文辉发电报让他炸毁泸定桥,一定要阻止红军过江。
刘文辉捏着这份措辞严厉的电报,在康定那间简陋的军部里踱着步。窗外是高原凛冽的风,吹得旗杆上的旗帜猎猎作响。他盯着电报上“务必彻底炸毁”、“否则军法从事”的字眼,眉头拧成了疙瘩。

为什么不炸断那座桥?
炸桥?炸掉泸定桥?蒋介石的命令听起来斩钉截铁,但刘文辉心里却在飞快地盘算。他太清楚这座桥对他意味着什么了。
1935年的西康还没正式设省,地广人稀,种庄稼的地少得可怜。可偏偏这穷地方,藏着几样金贵的宝贝:康定的虫草、理塘的麝香、巴塘的羊毛,还有雅安的边茶。这些东西要是运不出去,西康的老百姓就得喝西北风;可要是能顺着泸定桥源源不断往内地送,就能换回盐高原上顶缺的巴、布匹、铁器。
泸定桥是西康连接四川腹地的唯一咽喉,更是他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!每年几十万银元的过路费,支撑着他残存的军队和西康那片贫瘠之地的运作。炸了它?等于自掘坟墓,断了根基。
再说炸桥这件事,说起来简单,可真炸了以后,重建可就难如登天了。那时没现在的大型机械,修桥得靠人工打铁、拉链子。康熙爷修桥用了整整七年,动用了四川全省的铁匠铺。刘文辉要是炸了,哪有钱再建桥,而且上哪儿找这么多铁料、工匠?
到时候,炸了桥他没了经济来源,还得修桥,这对他来说百害而无一利。重要的是,他的实力大大消减,到时候西康的地盘能不能保住都两说。

更何况,刘文辉了解蒋介石的心思。这位委员长哪里是真想帮自己“堵截”红军?分明是想驱虎吞狼——让红军和他拼个你死我活,无论谁损失惨重,蒋介石都是坐收渔利的那个。
红军若是强渡不成,被消灭在大渡河边,蒋介石正好名正言顺地收拾他刘文辉这个“剿匪不力”的残部;红军若是拼死过河,必然也是元气大伤,他的西康军正好顶上去当炮灰。蒋介石这一石二鸟的算盘,打得叮当响。
“哼,想借刀杀人?”刘文辉冷笑,“又想让我出力,又想让我死,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!”他深知自己这点本钱经不起折腾。和红军硬拼,就算能暂时挡住,手下这点残兵败将也必然损失惨重。没了枪杆子,在弱肉强食的四川军阀圈子里,他就是待宰羔羊,蒋介石更会毫不犹豫地将他一口吞掉。
刘文辉身处那个各方势力角力的年代,行事从来不是莽撞之辈。他知道自己要是把底牌全摊开,准得被对方拿捏得死死的。所以甭管是战略布局还是日常周旋,他总留着三分余地,就像下棋时总留个"活眼",这叫审时度势的本事。
还有一种说法挺有意思,说他和共产党有关系。倒不是说他铁了心要入党,但至少没把路走绝。毕竟1935年,国内局势跟乱麻似的,谁能想到后来谁赢谁输?刘文辉作为川康一带的军阀,要是跟红军彻底撕破脸,万一哪天风向变了,他不就成了站在对立面的"老顽固"?所以他选择不把矛盾激化,该让步时让步,该缓和时缓和,就为给自己留条后路。

低估了红军的战斗力。
几番权衡,刘文辉想到一个“两全其美”的办法,或者说对他刘文辉最有利的方案。
他叫来心腹,下达了一个看似执行了蒋介石命令,却又大打折扣的指令:
“拆桥板!把泸定桥上的木板全给我拆干净,一根不留!”
他打的算盘是:拆掉桥板,留下光溜溜的铁索,表面上是执行了“毁桥阻敌”的任务,足以向蒋介石交差,表明自己“尽力”了。实际上,这既保住了桥的铁索结构,避免彻底摧毁这座关乎他经济命脉的桥梁,又给红军制造了巨大的困难。毕竟没有桥板的铁索桥,在常人看来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天堑。
这个做法,确实既能敷衍蒋介石,又避免了与红军发生大规模正面冲突损耗实力,最重要的是,保住了他日后重建的希望。然而,刘文辉千算万算,唯独算漏了一点:他低估了红军绝境求生的钢铁意志和超越常人的勇气。
他没想到,红军根本没打算按他的算盘走。当红军侦察兵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报告:"泸定桥的木板被拆了,只剩铁链子!"红军指挥部的房间里立刻炸开了锅。"没木板怎么过?""铁链子滑溜溜的,人走在上面能站稳吗?"可很快,有人拍了桌子:"没路就闯出条路来!当年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没,就是因为犹豫!我们红军可不能当第二个石达开!"
说到石达开,这事儿还得往历史深处挖一挖。1863年,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带领十万大军来到大渡河边,本来想在这里休整一下,再北上攻打成都。可他没想到,大渡河突然涨水,浮桥被冲垮,清军又围了上来。石达开想和谈,清军不答应;想强渡,河水太急。最后,他的十万大军被围困在河边,没吃的,没子弹,最后只能投降。石达开被押到成都砍了头,十万将士几乎全军覆没。
"咱们可不能让历史重演!""就算桥板没了,咱们爬也要爬过去!"于是,一个大胆的计划诞生了:组织一支精锐突击队,带着步枪、手榴弹,攀着铁链子冲过泸定桥,一边冲一边打掉对岸敌人的碉堡,为大部队开辟道路。
接下来的三天三夜,红军展开了和时间的赛跑。他们沿着山路急行军,饿了啃口干粮,渴了喝口山泉水,累了就靠在树边打个盹。有些战士实在走不动了,就被战友架着走;有些战士腿上划了口子,鲜血把裤腿都染红了,却咬着牙不肯掉队。因为他们知道,每多走一步,就离胜利近一步。

5月29日,泸定桥边响起了密集的枪声。22名突击队员扛着枪,腰里别着手榴弹,攀着冰冷的铁链子出发了。桥下的河水轰隆隆地响,好像在给他们加油;对岸的敌人发现了他们,机枪像雨点一样扫过来,子弹打在铁链子上"叮叮当当"直响。突击队员们一个个中弹倒下,可后面的战士又接着冲上去。
终于,第一面红旗插上了泸定桥的对岸!后续的大部队像潮水一样涌上桥面,踩着战士们用生命铺就的路,冲过了大渡河。刘文辉在桥对岸看得目瞪口呆——他怎么也没想到,这群看起来装备简陋的红军,竟然能在这样的绝境里杀出一条血路。
这场战斗之后,大渡河的水还在哗哗地流,可河上的泸定桥却多了一段新的传奇。22名突击队员中,有8个人永远留在了铁链子上,他们的名字可能没人记得全,但他们的故事,永远刻在了中国革命的史册上。
炸桥真的能灭红军吗?
要是当年刘文辉真把桥给炸了,能如蒋介石所想,消灭红军吗?
要是当年刘文辉真把桥给炸了,红军的处境确实麻烦大了些。先说说大渡河的厉害,光是站在河边看一眼,都觉得腿肚子发颤。要是没桥,队伍或许只能扎竹筏子。可更要命的是,大渡河底下全是暗礁乱石,竹筏子顺流而下,稍微偏点儿就可能撞得稀烂。就算侥幸过了河,竹筏子也得反复扎,队伍得一批批过。

同时,队伍还需在72小时内在百余公里河段重新寻找新渡口。不过当时国民党军已在所有渡口布防,要是抓住这个空子,集中兵力堵在别的渡口,红军想彻底跳出包围圈就更难了。最关键的是,蒋介石嫡系部队周浑元纵队距泸定仅剩18小时行程,时间窗口转瞬即逝。
再往深里说,泸定桥对红军的意义可不止是过河的路。那时候红军刚过了雪山草地,部队减员不少,装备也差,最缺的就是时间。如果能快速通过泸定桥,就能尽早进入相对安全的川西北地区,和红四方面军会合,那对整个长征的局势都是巨大的推动。
反过来,要是桥被炸了最坏情况真的发生。红军战前预案显示仍存备用方案,例如利用国民党追击部队薛岳与龙云争夺指挥权的内部矛盾,或许也会留出突围缝隙。
不过不可否认的是,红军成功夺取泸定桥这一战略行动,确实为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资源。通过这条关键通道,红军避免了长途跋涉的艰辛,有效减少了不必要的兵力损耗,为后续革命斗争保存了有生力量。
说完桥,再聊聊刘文辉。1949年的时候,国民党节节败退,解放军的队伍势如破竹,从东北一路打到西南。刘文辉知道,历史的大势已经变了。要是继续跟着国民党,就算暂时保住职位,等共产党来了,也得被清算。与其这样,不如主动站到历史这边来。
所以,他很快就决定:把西康和平移交给新政权。他先是稳住部下,接着他又派人跟共产党的代表接触,说明自己的态度:愿意交权。

这一招确实高明。西康和平解放,没打仗,没死人,老百姓的日子照常过,和平移交省去了不少麻烦。刘文辉这么一选择,算是把自己从"旧势力"的名单里划掉了,放到了"新建设者"的位置上。后来他当上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,算是得到了新政府的认可。一直到1976年安然去世,没再卷入什么风波。
泸定桥现在还立在大渡河上,铁索被风吹得叮当响,桥头的石碑虽然有些斑驳,但"泸定桥"三个字依然清晰。这座桥有红军的英勇,有军阀的算计,更有历史的选择。它就像一面镜子,照见了过去的艰难,也照见了人心的向背。
正规股票配资门户,天津配资公司,雷达证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